电影拉片——记忆、伤痕与新生
- 欧洲杯直播
- 2024-12-19 14:45:02
- 21
这部影片于1995年在日本上映,导演是岩井俊二。岩井俊二是20世纪90年代日本“新电影运动”的旗手,“新电影运动”是集中反映当代日本社会现实题材的一次电影浪潮。影片《情书》是岩井俊二的成名作。
电影《情书》是一部“青春残酷物语”,从中表现出来的,除了纯真中带有忧伤和离丧的青春,还有渡边博子和女藤井树的各自成长,或者说是重生。
1.主要人物:渡边博子、藤井树(男)、藤井树(女)
人物关系:男藤井树是博子已故的前未婚夫,女藤井树和男藤井树在中学时是同学
2.次要人物:秋叶茂(博子的现任未婚夫,同时也是男树生前的好朋友)、女藤井树的爷爷、女藤井树的妈妈
3.影片得以展开,有两个巧合:
(1)藤井树(男)、藤井树(女)两人同名同姓
(2)博子和女藤井树相貌非常相像
4.主人公不断错过,给电影蒙上了一层忧伤的色彩,其中主要有三次错过:
(1)男藤井树因山难去世,导致博子与他这段恋情的错过;
(2)男藤井树中学时期,由于内向和羞涩,没有直接向女藤井树表白,导致他错过这段青春时的暗恋;
(3)女藤井树对爱情比较迟钝,没有看书签背面的素描画,不知道男树借书卡上一直写的藤井树代表的是她,两人错过。
5.重生:
博子彻底和过去的恋情告别,接受了男树已死的事实,决定和秋叶先生开始新的生活;
一方面,女藤井树最终明白了中学时男藤井树对她的心意。另一方面,她的家庭关系改善了,她也不再沉溺于因父亲去世而带来的痛苦中,开始新的生活。
总体概括:渡边博子因为思念自己去世的未婚夫藤井树(男),无意之中在他家里的中学毕业纪念册里面发现了一个地址,于是往这个地址寄了一封信, 博子本以为这是一封寄往天国的信,不可能收到回复。但是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,她收到了来自藤井树的回信,经过进一步的书信往来,她了解到,这是与藤井树(男)同名的一个女同学。为了多了解藤井树(男)昔日的中学生活,博子与藤井树(女)开始了书信上的往来,在回忆的过程中,藤井树(女)发现原来男藤井树(男)一直暗恋着她。
一段结合升镜的长镜头。
需要大家关注的:镜头变化;画面构图;色彩;音乐片头第一段长镜头
(1)博子在雪地上前行,越走越快,镜头拉高,而后慢慢固定,博子的身影在远景中越来越小,越来越远,这种大片留白、黑白相衬的孤寂画面,留下了一种感伤的美感,将我们拉入博子悠长的思绪之中。
这一序幕式的段落里,导演采用从局部(特写)到整体(大景深镜头)的剪辑顺序,配合手持摄影与固定机位长镜头的拍摄方法,使影像呈现出一种日本和歌式的韵律。由手持摄影制造出的凌乱而晃动的画面暗示了生者的情绪,而最后沉静的固定机位的长镜头里博子远远离幵了雪地。通过影像的动态与静态的对立与融合,生动地表现了生死的差异以及由于生死相隔产生的悲伤情绪。
(2)钢琴曲《His smile》伴随着博子仰望天空响起,音乐节奏平缓,配上黑衣白雪的画面,给人一种忧伤的感觉,奠定了影片的基调。钢琴曲可以辅助表达博子对男树的思念情绪。
(3)雪在本片中有不同的涵义。在这个片段,博子躺在一片无边的雪原上,感受着雪的冰冷,也是对男树死亡时的感同身受。雪代表着对爱人的哀思,博子始终没能忘记这段感情,不能接受男树的死亡,还沉溺于过去的痛苦之中。雪容易消融,蕴含一种无常的哀感,很好地体现了日本特有的“物哀”美。
黑衣和白雪的对比,引入后面祭奠男藤井树死亡的情节。
接着是藤井树去世两周年的祭奠式。我们可以发现,博子身边的人们,包括死者的父母和友人,已经用遗忘象征地埋葬了死者。父亲迫不及待地等待仪式结束后一醉方休,母亲不无顽皮地假称生病逃走,昔日的好友秋叶茂托辞缺席,却私下约定夜半前来探墓,似乎这是一种有趣的游戏。只有博子双手合十,独自站在墓碑前。只有博子拒绝遗忘男树,也无法遗忘这一份忠贞的爱情。这呼应了影片反复重申的关于死亡、重生与记忆的主题。藤井树的家人、朋友已经释然
这段是博子送男树的母亲回家之后的情节。这里有两个值得关注的小细节。细节一是男树的房间里有好几幅画,都是画的山,这从侧面反映出男树对山的热爱,也呼应了男树因山难意外去世的情节。细节二是,男树的母亲给博子看了一本男树中学时的毕业纪念册。因为男树没有读完初三便转了学,所以这里男树的照片没有出现在众人的大合照中,而是单独出现在右上角。男树的母亲看了这张照片后说:“现在看这照片感觉不太吉祥”。画着山的画、看起来庄重严肃甚至“不太吉利”的照片,似乎早已预示着男树后来因山难不幸离世的悲剧。
博子送男树的母亲回家后,男树的母亲给博子看了一本男树中学时代的毕业纪念册,博子看到了那时“藤井树”在小樽所居住的地址,并悄悄把它记了下来。一个有趣的细节是,博子起先要将地址写在手掌上,继而改变了主意,挽起衣袖,将地址写在自己手臂的内侧上:这无疑是为了避免不小心抹去了手心上的字迹,但它同时也构成了一种写在自己的身体上,写在自己的隐秘中的视觉呈现。这封情书有着相当普通的词句,只有这样几句话:“藤井树君,你好吗?我很好。渡边博子。”正是在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问候中,透露着巨大的痛感:拒绝死者已逝、阴阳相隔的事实,祈望死者犹在。
“信”的作用:推动情节发展。博子和女藤井树正是通过信来交流,从而一点点地揭开真相的面纱,即博子渐渐明白男藤井树对他的爱只是“影子之爱”,她是女藤井树的替身;写信帮助女藤井树回忆中学时和男藤井树生活的点滴,片尾她发现借书卡背面画的是她,她最终才知道中学时男藤井树暗恋她的事实。整部电影分为渡边博子和女藤井树两条叙事线,多次运用了平行蒙太奇在二者之间进行切换,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两个人写信和阅读来信的这个情节。
(戴锦华教授的《电影批评》一书中借助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分析了电影《情书》)
在精神分析的视域中,博子寄出的这第一封信具有双重含义。
首先是,博子她希望沿着缺席抵达在场。我们无法将朝向死者的问候与无穷的思念寄往天国,那么似乎可以将它寄往一个真切的人间的地址,一个同样已死的地址:按照死者母亲的说法,他们彼时的住宅已变成了一条公路通过的地方。寄出一封普通平常的信件,似乎是最为微妙而准确的表达:拒绝死者已死的事实。但同时,寄出这封信件,间或出自某种潜意识的愿望:她所真正希望着的是印证缺席。这信在发出之时已然获知,那是注定无法送达的、名副其实的“死信”。博子告诉秋叶茂这个令人惊喜的消息时,也对秋叶茂说:“我是因为寄不到才寄的,那是寄给天国的信。”
博子从未想到这封寄往“天国”的信会收到回复,没想到真的收到了回信,回信的内容同样很简单,“我很好,只是有点感冒。”感冒——这个相对于“天国”回信而言如此平凡的细节,在浮现出几分荒诞感的同时,又传递出强烈的真实感。因此,博子才满心欢喜,并将这个“奇迹”分享给秋叶茂。秋叶茂当然清楚,这封回信绝对不是他们所认识的那个藤井树写的,因为男树已经死了。为了解开这个谜团,秋叶茂以博子的身份给女树写了一封信,要求她证明自己的身份。女树回信过来,这个谜团终于解开,原来,这是一位与男藤井树同名同姓的女子。秋叶茂为了彻底打消博子对男树的幻想,决定带博子去这个女藤井树居住的地方看看。
秋叶茂带博子前往信件寄往的地址——小樽,也就是藤井树初中时代的家来探访。三人走在积雪的路上,逐个辨认着门牌,走进了公路桥下的涵洞。中景镜头中,走在前面的秋叶茂和他的朋友突然发现博子并未跟上来。他们转过头去,摄影机升起来,越过两个男人的头顶向前推,全景画面中,我们看到博子独自站在积雪半溶的涵洞边,站在光与影的分界处,在孤寂中自语:“第一封信应该是寄到这里的吧。”画面中的元素,包括覆盖着积雪的、没有任何生命迹象的高速公路,钢筋水泥的公路桥,涵洞投下的浓重阴影间,站着黑衣的、忧伤的博子。这似乎再次重申了死亡与重生、记忆的埋葬与钩沉的主题——寄给男树的信是为了否认他的死亡,但也是为印证他的死亡。
接下来镜头切到了医院里,女树的妈妈以看新房为由把女树从家里带出来,实际上却把她带到医院让她看病。
需要大家关注的:光线;镜头;蒙太奇;色调
女树在医院曾产生短暂的幻觉,幻觉的场景是她爸爸抢救的画面。
注:下面是一段文字一组图占一张PPT,蒙太奇那个可以多占几张PPT,图片大小你们自便,只要版面合理美观,不拉伸变形就OK啦(点图片斜对角可以成比例放大/缩小)
光线:这里使用逆光制造了一种虚幻的不真实感,光晕笼罩,女树的耳边却传来她妈妈叫“藤井树”的声音,直到她忽然惊醒,发现是挂号的护士在叫她。
镜头:母亲和爷爷出现时,二人转身望着走廊这边的藤井树。岩井俊二在这里使用了连续的正反打,母亲和爷爷与女树的对望,三人脸上俱是担忧。在医院女树出现幻觉时,她跑向父亲被推走的地方,镜头此时是忽左忽右大幅度倾斜角的拍摄状态,也体现出人物此时心里慌乱不安的状态,包括暗示了这是幻觉。升格镜头以及倾斜摇晃的走廊显得她的奔跑格外缓慢与艰难。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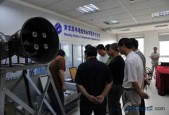







有话要说...